浮于野 by 刘大风: 鼎盛、灿烂的公共性景象是我所憧憬的 | 三明治 · 空间跳跃

“浮于野书店是一家认真卖书的酒吧”,这既是他们公众号对自己的调侃,也是事实:浮于野的左半边是书店,右半边是酒吧。在听浮于野的 80 末主理人刘大风谈论这间只卖诗集的书店时,经常会忘记今年 2 月 14 日情人节在成都开张的它至今还不满半岁。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浮于野办了盛况空前的百日宴和一场野地里的诗歌派对。它几乎没有常设的店长,而是经历了 82 任轮值店长,他们贯彻浮于野“民粹”和“去中心化”的宗旨,除了自选诗词写在门口的小黑板上,他们还在店里给读者们荐诗、带领大家读剧、和大家一起观影(后来观影活动被正式定名为“坝坝电影”)。此外,银弧诗会举办了 11 期,参与者一起读新诗、读老诗,也会读读自己写的诗。每期诗会的收入一半给活动组织者,另一半归入“银弧写作基金”用来支持写作者。浮于野还有同样“民粹”的线上主题沙龙和播客等待上线,可以预见的是,刘大风和书店读者们的联手折腾绝不会止步于此。


浮于野百日喜酒派对


坝坝电影
两个月前,刘大风宣布即将在成都太古里旁开设总面积达 2000 平的二浮(二号浮于野)只卖小说,安居街上的这间小店便升格成了大浮。二浮以书店为中心,还包含了民宿、酒吧、咖啡馆、独立服装工作室、和定制西服工作室,预计八月中下旬开幕,就在这个月。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运营大浮,策划、落地二浮的同时,刘大风竟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互联网大厂打工人(至今依然是)。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在疫情未散的当下,坚持扩大线下规模?
以下是刘大风的自述


浮于野书店位于成都武侯区双楠街区。
双楠是成都最典型的那种老街区:附近的房子很旧、楼层也不高,墙面斑驳,白色的油漆早已变成了灰色,也没有人去修缮。这些房子的不锈钢防盗窗都已经开始起锈了。走过这个街区的人,可能是一群体型臃肿的中年妇女,或者是身体佝偻的老年人,还有一些学生,当然也有部分的年轻人。这里曾经也是成都著名的酒场,至今还有一些灯红酒绿的地方,包括一些比较暧昧的场所。可能在浮于野附近三四百米的某条暗巷里,就藏着一间情色旅馆。这个街区整体来说是陈旧的,甚至是有点过于老化的。
浮于野说起来其实是在一环旁边,在一个很有内城氛围的地方。书店所在的安居街是一条次级干道:如此一来,它虽然不在主干道上也会有车经过,相对来说又比较安静。街道两边有人行道,人行道上种了很多高高的树,树荫会落在书店门前,因此可以在那里摆几张椅子。书店旁边有个学校,上学、放学的时段虽然很热闹,但是孩子们不会走进书店,他们只想着考学,只想读课本、读教材。

如果你在午后的两三点坐在浮于野门口,你会看到汽车少了、街上的行人也稀稀落落的,附近店铺的店主都开始打哈欠。也许能听到蝉的声音,因为挨着机场所以偶尔还有飞机的轰鸣声经过。在这里你能感觉到这个城市的肌理向你裸露出来,那种宁静是城市经过时间的淬炼之后才能够浮现的。
虽然我们很多的会员都是附近的居民,但浮于野不是一家社区书店。总体而言,浮于野 80% 到 90%,甚至 95% 的读者都来自各方。他们可能来自成都的各个区域:连住在双流、华阳、天府新区、新都、龙泉这么远的地方的读者都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来自上海、深圳、大连、安徽、山东......的读者从网上认识了我们之后慕名而来。对于这个状况我并不意外,因为一开始我给浮于野的定位就是要做有更深远、更广阔影响力的书店。
在疫情时代开书店当然是逆势的,但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欲望是比较强烈的,所以无论是书店行业本身的境况,还是时代的境况,我不太在意这些外在的条件。
独立书店和线下实体书店的困境其实是很明显的,网络电商对书店的冲击是致命的。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大家买书、甚至看书的习惯都改变了。人们改看电子书,实体书则倾向于在网络电商平台购买,因为平台上的价格极具竞争力。
电商平台花重金给书打折、补贴,是因为他们明确地把书籍看作平台营销战略中的流量抓手。人们在网上能买到六折、七折的书,这跟出版社给线下书店的批发价差不多,所以线下实体书店是绝对卖不赢线上的。我经常跟朋友聊到,其实线下实体书店已经死了,它原有的存在逻辑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了。
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一种进步。在互联网兴起之后,读书、买书都很方便,所有人都有一个触手可及的图书馆。打开手机,人们就能找到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好的书,且一秒钟就能买到它。互联网加速了人获取知识、思想、信息的条件和形式,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需要去改变的势头。它是历史的时势,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无法逆转的:人类就只能这样读书、买书了。
开一间书店确实是不太理智的选择,我主要是受到一些情绪的牵引。即便我们面对的是这种形势,但是我和可能很多其他人还是喜欢、怀念线下的实体书店,这是浮于野存在的基础。
很多时候线下实体书店的书被卖出去是包含情怀溢价的,但是我不太认同这个东西。我认为书店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如果它不依靠刚性需求、没有稳固的基础需求,那不是长久之计。
线下实体书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存活。不避讳地说,现在大部分的书店都变得挂羊头卖狗肉,这是行业现实。咖啡、茶饮都救不了今天的书店,只有酒才能让书店续个命。浮于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是靠卖酒,酒的利润很高,比如 58 块钱的一杯调酒成本是 10 块钱,血赚。我经常自我调侃“把书店变成水吧”,这就是让独立书店还能够有一些收入的手段了。浮于野另外一个支柱是会员制,书店一次性得到一笔会费,可以让它支撑下去。


支持浮于野的除了强烈的欲望、水吧和会员收入外,还有一个原因:我还在上班。目前我是某大厂打工人,所以开个书店有点像我的一个玩具或消费品,就算亏了也没有关系。每个月的房租是 7000 块钱,水电费可能是 1000 块钱一个月,人工成本至少要 5000 块钱,一个月的运营成本最多是 15,000 元。我预想的是我每个月亏 7000 块钱都没有问题,因为这确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压力。但是它不能一直亏,一直亏说明没有人来、没有人喜欢它,我养着它就没有意思了。
现在发现浮于野活得还不错,大家喜欢它。我们在第五个月的时候迎来了赢亏平衡点,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赚够了下个季度的房租。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它以后就是纯赚了。
卖茶、卖咖啡、卖酒有点接近我前面提到的为书店添加刚性需求,但因为产品力不够这也只是一个折衷方案,某种意义上人们还是因为氛围来消费。二浮将会有的民宿、高定西服工作室、时装工作室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些符合市场逻辑的、硬核的产品要让浮于野作为线下实体书店可以体面、独立、硬气地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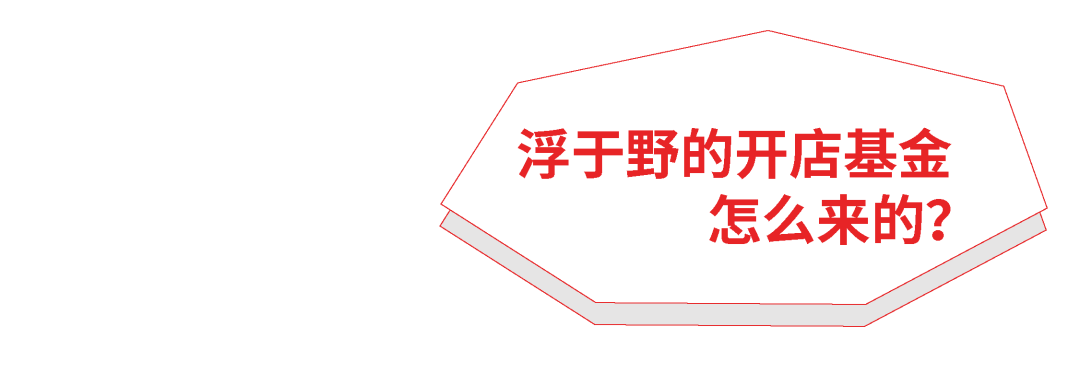
浮于野书店为什么开得起来?这主要是一个资金问题,在我理解中它是一个取舍的结果。
简单讲,就是我把房子卖掉了。之前因缘际会在杭州买过一个房子,后来升值,我选择直接出手,大概赚了100万。而卖掉杭州的房子,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它背后的整套生活模式,以及这个城市。按照当地政策,二套房需要六成首付,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不可能再付得起这个城市房子的首付了。
本来,是不会有这段经历的。三年前,我爸重病,我去跟各种大学同学、朋友化缘,化了 10 多万块钱把他给救活了。为了还这笔债,我选择去杭州打工,在无奈中离开了媒体行业。我在上班的时候发现我的公积金非常高,那笔钱躺在那里不用很可惜,要用就只能买房。而当时杭州的房子首付至少 80 万起,我肯定是没有这个钱的。
那时候着急要买这个房子,是因为我家很穷。我爸妈都是纯而又纯的农民,为改革开放的建设在广东、苏州打了一辈子的工都是租房住的,所有的钱都花在我这个小镇做题家身上读大学去了。爸妈的出租屋都破破烂烂的,那时候我们过年都没地方过,所以在杭州买个房子也是有必要的。
当时我拜托同事、朋友给我腾挪资金,加上杠上天的杠杆,我只用了 10 万块钱就在杭州买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后来把房子出手,首付还清了、债也还清了,还多出一大笔钱来。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机,我拿这笔钱应该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把那一套要负家庭责任的说法完全抛之脑后,我觉得我要去大理,我要揣着这笔钱去一个地方隐姓埋名、过阅读写作的自由生活,这笔钱能花个好几年。这种没有良心、没心没肺的想法过去了之后,我最后的方案还是回到成都。
杭州那套房的 100 万就是浮于野的开店基金,而且还让我负了一点家庭责任又重新给我妈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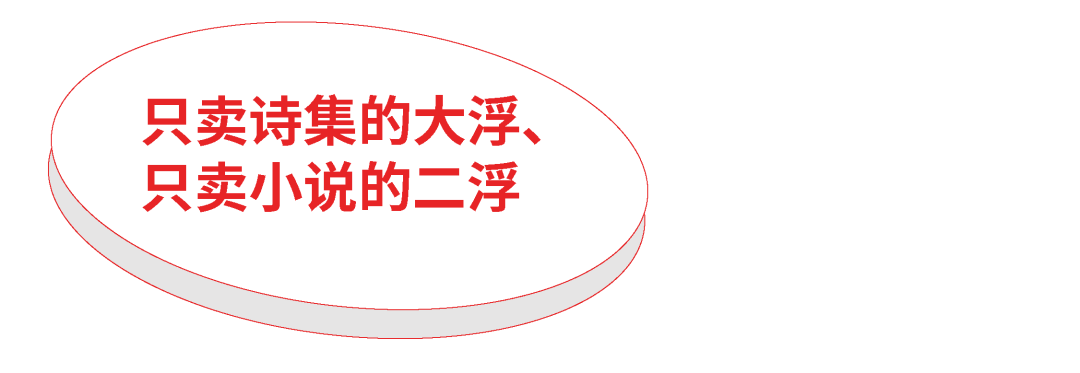
本来开书店这个想法只是偶尔一提,因为我自己肯定还是想当一个写作者的,我不喜欢给大家服务,开书店就是给大家服务了。后来明确说要开书店大概是在去年的七八月份。当时的动因是焦虑:我想在上班和写作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上班时人会被世俗里物质的东西裹挟,写作和阅读如果不在一个职业和专业的状态,很容易就被抛弃了。因此我想要给自己找一个锚,把自己拴在知识的领域里面,让自己的精神能够有更多的依托。工作、阅读写作、加书店就形成了生活的稳定三角。我有一个书店,整天需要打理书,我肯定就会读书的对吧?这样我就不会因为工作而完全偏离一个严肃的思考者、写作者的方向。
浮于野在半年之内做出此刻不错的成绩,我肯定是有点意外的,但也没有太意外。在整个浮于野的运营过程当中,我最激动、手抖的时刻发生在没等工人们把装修灰尘扫干净就迫不及待去拆书的那天。我一边把书摆到书架上,一边录视频发给朋友:正式的上场了!现在这里摆着柜子,它只是个店铺,但是书一放上去,它就是个书店了!

后来我会刻意地让自己不要激动。我需要一个大心脏来面对可能来临的风浪,所以一惊一乍的不好。做事要追求目的性、功利性强,追求一定要把事情做成,不能中途开始庆祝。后来浮于野取得很多的进展,比如我们的公众号读者上涨了、我们的活动能有一、两百人来参加,我都选择平静面对。就连我去签二浮的字时我也非常平静。甚至我们在 7 月底时发起的众筹至今已经筹到 20 多万了。对于一个独立书店来说,纯靠读者和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筹到这么大一笔钱,我只能觉得还不错、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但也没有特别的激动,因为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
大浮选择只卖诗集的原因有四个,除了纯粹的喜欢,也有很多策略性的考虑。
第一,我喜欢“一家只卖诗集的书店”这个设想,有一种宏伟和浪漫的气息笼罩着这个书店的感觉,这样的幻想让我非常爽。
第二,只卖诗集让库存很轻省。如果要做成百科全书式的书店,可能要囤价值二、三十万元的书,这会直接拖垮书店。而卖诗集只需要专注几百个诗人,不但不需要进太多的书,还能够营造一种专业感。这种成体系的感觉暗示浮于野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有规矩的书店。
第三,一个主题书店更加容易运营。要让书店活下去,就得让它变得更有意思、被更多人关注。今天的浮于野在大家眼里有点意思是由它最初的设定决定的。
第四,这个设定让我们的书变得更容易被产品化。诗集在浮于野变成了一种产品、一个礼物;再俗一点,我们可以把书纳入“新消费”的概念里面。这个概念虽然是人造的,但也揭示了一些现实性,它是指我们把产品纳入到更接近都市年轻人日常生活、消费的场景里。包括二浮的设定是只卖小说,也是为了让书变得更像产品。
如果有人问我推荐哪本诗,我会主推两个方向:首先,我会推荐活跃在 20 世纪的国外当代诗人的作品,也就是生活经历跟我们相近的这群诗人,读者更能从中获得共鸣感,阅读起来也没有太大的门槛。然后推荐国内当代不那么知名的诗人的作品:当下还在中文圈子写诗的无论年纪的诗人,只要写得好我们就愿意大力推广,银弧诗会也会首推他们的诗。



诗会
而二浮之所以只卖小说也是为了保护大浮。如果二浮的出现导致大浮活不下去,这是我不想看到的局面。因为浮于野的读者也就这么多,甚至可以说读书的人也就这么多,成都市作为全国书店数量排名拔尖的城市,读者都不够用了。考虑到这一点,二浮是绝对不会跟大浮抢生意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大浮设置很多保护机制,比如说把重要的、精品的活动放在大浮举办,还有把特定权益留在大浮。

书店里面显眼的地方展示了一首名叫《一个女人》的诗:
一个女人失去故乡
和自己的父母
失去名字
和自己的房间
失去衣服
和自己的通讯录
失去睡眠
和自己的语言
失去牙齿
失去春天
失去指纹
失去下雨天失恋
失去马桶圈
失去疯癫的自由
她可能是被拐卖了
也可能只是结婚了
这是一个朋友写的,表达了我们书店的某些意思。

作为一个直男,非常典型的农村长大的男孩子,一个五大三粗的田径生,一个充满了大男子气概的人,一个男权社会、文化结构的受益者,我觉得我没资格谈女权,没资格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只能说我对女权议题有一些关注和涉猎,我直觉地认为有一些必须被张扬、弘扬、捍卫的价值在其中,然而我的行动是不足的。我身边很多朋友愿意告诉我他们惨烈的受侵害的故事,很多人也深度地介入到女权的行动中,他们承担和付出了很多东西。我只是在旁边当个小喽啰,给大家加油鼓劲、听他们的故事,也因此受到感染。
浮于野当然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女权取向的书店。比如提行出品的第一件衣服,它就是一个张扬女权概念的产品。我们的读诗团也会刻意地让女性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以后我们为二浮组建施工队的时候,也会更多地让女性出场,来赞扬女性身体的力量。

提行001号作品



二浮拆墙前的涂鸦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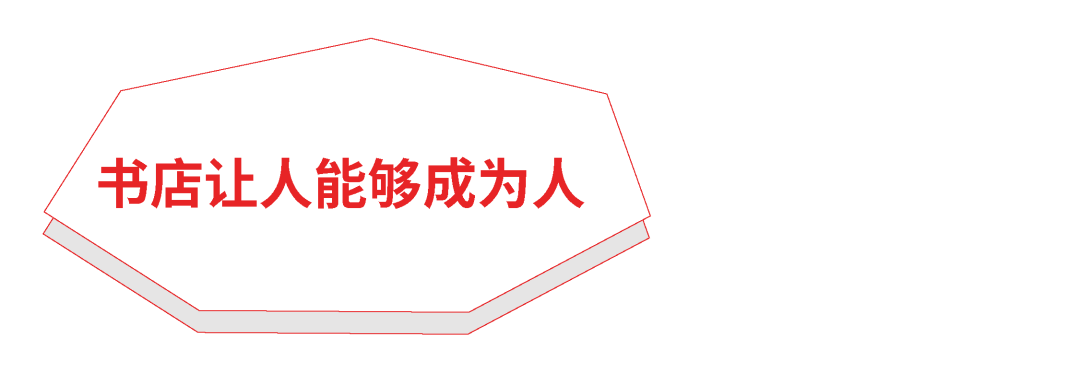
在杭州,我经常去单向空间,因为那儿很舒服。坐下之后我会点一杯红茶,然后泡一整天,直到茶叶表皮都泡烂了我还在书店里泡着。我喜欢在那里读书、写东西,书店的空间足够大,给人一种可以消失在此的感觉。二浮的设定也是这样的:它当然要有社交属性,但它同时有一个大空间让人能够消失在里面,读者可以在那个空间里沉浸到书本和创作中去。
社交和消隐既矛盾又不矛盾。
本质上我不是一个非常 social 的人,我喜欢跟朋友一起玩,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比较功利的社交场合,很多时候更愿意跟自己待着。我既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家庭,处在一个完全独身的状态中。我很享受独身,保持自由是为了向更多的可能性去展开。当然我也有正常的欲望,一些和荷尔蒙、多巴胺相关的东西,这确实是一个自由的难题。
我提炼了很久,到底孤独中令人着迷、痴迷、沉醉的是什么?那是一种“独自面对宇宙”的感觉。你可以想象我在书店跟大家聊了一晚上,午夜我独自开车回家,经过空旷的公路,一路都不用踩刹车。我掠过城市辉煌的灯火和郊区的灰暗,回到我的家。一路上我不用想着跟谁联系,也不用跟谁打招呼。我也许听一会儿死摇,或是听一会儿贝多芬,也可以什么都不听就那样哑默着,周围只有风声、胎噪、和发动机的转动,这种状态是非常美好的。
处在这种独自面对宇宙的境况里面能够成就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比如我写诗时就必须在这个状态里。我必须独自一人向世间的喧闹背过身去,我得朝向荒野、朝向空芜的或者说浩瀚无边的宇宙,在那里让词语开始跳动,让意象开始萌发,然后让句子开始生成,让整个世界连接起来,让诗意不断地折叠、跳跃、变幻、飞升,然后升华。我觉得只有在孤独里面才能够成就艺术、创造美,我此生都必须保留独自面对宇宙的权利和可能性。并且,在某种不是诗学而是公共性的意义上,我们今天也很有必要捍卫孤独。
从另一方面看,我也不会沉浸到自我的世界里出不来,我营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能非常真诚、热烈的跟大家去营业。我还是很喜欢 party 的,喜欢参加开心的派对,跟大家一起喝酒然后整晚瞎聊天,等到天光泛白的时候才离开。我是个享乐主义者,派对上面发生的一些奇怪的、偶然的、浪漫的、跳跃的、激情的、闪烁的东西是我很喜欢的享乐。
开书店更多的是一种公共性的实现:让我能跟更多人在一起,能让更多人在一起,让人们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走到外面的人群中,走到我们的世界里来。我写过一篇日志标题是,那种鼎盛、灿烂的公共性的景象是我所憧憬的,也是我做这些事情的根本动力,是让我走出独自面对宇宙这令人沉迷的孤独感的很重要的动力。
有段时间因为忙着二浮或工作的事情,我会不经常去书店。然后当我以一个普通读者而不是书店店主的身份走进浮于野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那种令人沉迷的精神气息外化成了一种可触碰的质感,它甚至会从你的皮肤表面滑过。
这种精神的氛围是具有超越性的,它是高于地面、漂浮在半空中的,它是与天上的东西有连接感的。这种精神的氛围呼应着每一个普通个体本身就存在的超越性。人的超越性可以在书店这个地方被触摸到,被呼应、被唤醒,然后被更多地阐发出来。某种意义上书店就是让人能够成为人的地方,这就是书店对大众的价值。

· · · · ·
三明治“555 Project”自2021年1月推出以来,在“在地”领域呈现了近两年上海街区发展的生态,并连接了很多在地的创作力量。现在,我们正推动555 Project走向全国,共创更多在地项目。由此,我们想到设立一个“555 Project在地创作”支持计划,给在地创造上有需要的朋友帮一把。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