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对话||杨键再次对话余退
一道月光进来,她甚至要忘了女儿身
把被子拉到脖颈以上
躺进一面无比巨大的黑镜子里
她不可思议地看到自己
光洁的头,散发出软绵绵的反光
千层饼
头层和底层何其相似,金黄的表面:
你们是天生一对,至少理应如此
想象过于酥脆,第二层隐约可见:
命运迷人,月亮是枚定制的钻戒
绿色的葱,焦的皮,切忌小题大做:
碗筷袜子爬爬垫与爱的交谊舞
某层夹生,或许这一切有点假:
眼神冷漠,猜忌的枕头,有了鼾声
如果味道太淡,这恐怕是必然的:
好姐妹,小捣蛋,他们带着调味品
不分你我的时刻也是有的,天啊:
一百万次融化石头的坚硬,成为合金
遗忘的情书,相信会被尘埃找回:
马上来!你先吃。我在等山雾散开
叠起来,他和她不过是半透明的
结婚证:一张薄薄的千层饼
混血果
走进果园,当我见到青涩的
嫁接植物,并没有认出异类
绿叶遮蔽着,像一群穿校服的
中学生,会在某刻自行脱落
飞翔,滚动,货架上,提袋里
将到处都是
像是云端顷刻而至的伞兵
如果移栽,原始森林的猴子们
会亢奋地尖叫,来不及辨认
舌头上模糊不明,当榨成果汁
味蕾进行着一次重新定位
或许,每次篡改都挣脱出一次
创世。它们将不再返回
此刻,它们缄默地挂在晚雾中
章鱼
爷爷说起过某年海水倒灌
一群章鱼冲到稻田里
本能驱使它们遁入泥淖
将自己活埋。粘稠的身躯里
本就没有预设骨骼
我记得杀死这种软体动物时的
艰难。有次父亲抓住章鱼的触须
将它往老厝石壁猛摔
绵软的身体发出湿漉漉的撞击声
绝望的吸盘吸住了石壁
和我父亲的手臂
我不会忘掉那生与生
坚韧与坚韧间搏斗的场面
仅仅旁观就镜裂了我的蠢蠢童心
集体症侯群
我太了解那凑热闹的感觉
在大潮里走神,人挤人训练出的
得失心,每挪一步涌现的欣喜
我是斤斤计较的人,和两个妹妹
不同,早两年出生营养的短缺
发育出我的五脏。我向她们说起
当妈妈给我两块钱摸彩时的
亢奋感。梦想扛回彩电
当我慢慢刮开涂层,从无关
紧要的尾部刮起。等里面的数字
发光。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里
总有一位幸运儿,他像是
把所有人的灵魂都叠加起来
大家都高兴坏了,妒忌,差点
以为是自己中彩了。由此我
得到孤独的特效药:排在长队里
或一拥而上,哄抢免费发放
印有“宣”字的日用品
人工欢愉
有人在制造欢愉,配音版的笑声
作为背景音被适时插播
其实格格不入,像有人在替我们笑
替我们活这略显乏味的生活
说也奇怪,我们会被机械的欢乐
鼓动,分不清违心还是不违心
不管多虚幻多无聊多没用多干旱
就浅表的沉迷也好,像儿时吃糖精
放一点点在面团里,就觉得够味
我们这些食用提取素的人
不可缺乏那股沁骨的秘制甘甜
染发
耳廓微微发痒,潮儿们耐心等待着
漂染的洋气。女青年将自己罩在
圆形烫发机内,在缓缓溢出的蒸汽里
漫步于太空。两鬓成霜的大叔
惊喜发现小部分白皙头皮也染黑了
推开时间的翻转门,父亲俨然
成了这座新小镇的美学工程师
穿着一袭深色西装,打着枣红领带
与慢慢发胖的母亲忙活到深夜
不知疲倦为跨进店的顾客
换容,仿佛他们是落魄已久的上帝
理发店拥挤着各种新奇的时事
当时,未来尚且是不确定的
在半身镜与半身镜无数次的折射里
我拿起大功率电吹风练习着出神
像一片开垦地
钻机击打水泥地面,大地微震
露出的土壤层,像一处洞穴
正跛脚通往苏醒。深埋的种子
和我们一样数量庞大,更耐心地
等待雨水,未被摧毁过一般
总有裂缝带我走向降落的秋季
扛着农具,我跟在母亲身后
去收获番薯。喜欢闻开垦地上
烧草木灰的味道,黄昏
将汗吸干的感觉
像此时低空中柴油味弥漫
禁 忌
抱膝飘荡在海水中,如果睁开
双眼,我总是能看见沉船
当电梯快速上升,狭小的密室里
站得笔直,我知道上端有一股
垂直的力拉伸着幽暗。和祖辈一样
我获取了所有渔家命定的禁忌:
小时候母亲不让我去游泳
不让我跟着去扫墓,到草绿色的
病房内探望病人。我也不希望
女儿过早拥有不可逃避的苦难意志
可以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兴奋地
期待末日降临,看上去如此晚慧
当我发现夏季正午下的露水
晶莹着,保持着近乎士兵的克制
滚烫,竭力不被蒸发,会有迫近
中年的男人少有的猛烈感动
众多碎片
在瓯窑小镇,双瞳的王师傅
带我们看修复后的宋瓷瓶

白陶土所粘合出的坍塌锥形
在他的指引下,我也能辨认出
破碎之物才具有的双重世界
摔碎的手机屏里,我的黑脸
带着一道道隐裂的闪电
像脸上有疤的人,正从疤痕中
萃取沉寂。坐在海边丢石子
平静的海面一次次打碎
又复原。海面里的他又一次
凝合。偷偷拆走小朋友们
耐心搭建的乐高塔里的
一扇方形窗户,或其他小零件
无人处,他低头用收集到的
众多碎片,拼接整座失乐园
带着电筒
走夜路。在一束光里。被照见的
物体发亮,但不多,不远
隐秘的世界正在返童,风会
揭下蒙眼布。我注意到
冰凉的水流,鼓荡着整座田野
直至天穹的蛙鸣,头上星光
爆裂的噼啪声,都不容易被
照得太清晰。真是奇怪
在一晃即没的大部分
漆黑里,总有一种明亮感
沿着电杆排列的方向,我走进
带交流电的房子。我醒来
没有注意到我始终
拿着打开的手电,直至熄灭
夜间行车
脱离尾灯的光带,随某个拐弯
驶入大面积空旷的漆黑
光斑与光斑的刹那相继里
你努力辨认幽暗中静止的事物
微微摇晃的影子。来不及看清
他者,或许那是某位因爆胎
而停留的异乡人点亮了一根烟
找到夜游的动物,猛地刹车
路中间蛰伏的绿眼猫一跃而起
不知悬浮在哪段未明的时空里
像琴师的手在幻象之琴上弹奏
沉浸于隆隆的白噪音——
混沌之乐自黑暗内部向外弥漫
你就这样独自驾驶着,感动于
与夜海涌为一体,直至抵达
某个岔口,前方的强光唤醒你
黎明将梦游者拉回到枕头上
黄金甲
梦中的金鳞在海底游动黑暗
外公说起关于丰盛的恐惧:
当敲罟作业带来的大黄鱼群成灾
堆在厕所边腐烂,鱼臭味漫天
腌制着渔村。金银两色鱼鳞飞扬
像大海发行的冥钱。他们
祷告海神杨府爷,祈神力洇灭
贪婪,阻止鱼群求死的信号
在深夜捕捞的大黄鱼才会拥有
迷幻的金黄色。阳光下它们的
鳞片会苍白。在夜间观海时
我破解出了六郎的护佑败亡的
原因:崖山跳海的将士
重披荣耀的金甲,错听擂擂
战鼓,以鱼身冲陷阻隔它们的
细密渔网,一轮轮,一群群
赴死,哪怕无限次亡国
杨键再次对话余退
杨键:你的诗歌美学是什么?
余退:我注意到了诗歌的“空无”属性,诗歌发乎心灵,其本身是透明的,具有反逻辑的“歧义”特质,可以在不成立处成立。它在,又不在。诗歌的写作犹如悬浮,可以让庞然巨物悄然腾空,又仿佛为人穿上隐身衣,让实体之物瞬间不见。文字本身是具有“魔性”的,中国传说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组合而成的一首诗更像一道符令,看上去笔划凌乱,但是它用自己的语言替万物画像,替万物开口,讲出了万物的沉默,却又若有若无。
杨键:你的困惑是什么?
余退:困惑很多,人生有诸多无奈,最大困惑是关于生命的困惑,比如身心的安定,价值的确认,自他的超越。生命的境况多变,很多冲突和矛盾之处,此起彼伏,看似有些问题有答案,实则效力不高,困惑盘踞不去,或许是困惑本身在带领着我们行走,我有一首诗《迷惘而坚定》写过“艰难走向精神之地的/诸多岔路,朝着临时性的/目的地,我的迷惘从未如此/清晰。”
杨键:诗是什么?或者说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余退:诗依旧是神秘的,诗是什么很难说清楚。沃尔科特说“我从来没有把写诗和祈祷分别开来”,他几乎把写诗等同于祈祷。从我的理解而言,诗更像是一扇窄门、一条地下通道、一艘潜艇。好诗的标准也很难定论,或许是好诗定义了“好诗”自己,正在出现或尚未出现的好诗将再一次定义“好诗”自己。
杨键:新诗成熟了吗?它还缺什么?
余退:新诗100年,肯定不够成熟。“物壮则老”,新诗不成熟或许也是我们的幸运之一,留给新诗诗人拓荒的空间比较大。新诗所缺的东西可能非常多,个人感觉有两点不可忽略:一个是新诗精神内核的养成,这个是需要再次辨识、自我赋予的,需要一代代诗人心传和坚守才能形成的;另一个是生命力,新诗之“新”就在于生命力,生生不已,源于本真,甚至带有盲目的冲动,缺乏生命力的诗歌则死气沉沉。
杨键:旧诗之“我”同新诗之“我”有何区别?
余退:旧诗之“我”同新诗之“我”有同有异。同则是诗性之我,有别于现实之我,诗性之我很多时候是隐藏、蛰伏着的,通过古诗或者新诗都能够实现和内心的自我对话,和隐秘的世界漫语。异则相对旧诗之“我”,新诗之“我”更加具体、低沉、碎片化,更能直面真实之境,其表现空间更加自由和巨大,也更加无序、苦楚。“现代诗鼻祖”波德莱尔《恶之花》所开具的诗意就有别于经典时代,写丑恶,写忧郁,写困境,比如“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太阳沉没在自己浓厚的血液里”。但新诗之“我”依旧能够穿越现实之境直抵精神之境之间,这个是诗的属性所决定的,这个“我”依旧是超越的。
杨键:林纾当年翻译《茶花女》,辜鸿铭几乎以死相抗,现在细想,辜鸿铭当年所反对的郑声,在今天几乎成为现实,也就是说,汉语在今天已经严重地物化,欲望化,正是孔子当年反对的郑声,这就是目前汉语的现实,对此,你如何看?
余退:林纾翻译《茶花女》,辜鸿铭批判林纾,各有其立场和价值。社会的物化,有现代化推进的原因,也有我们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独特原因,现代汉语也随之具有了物化、欲望化的倾向。古代另有文言系统以对抗语言的世俗,诗更是天然具有抵御世俗化的属性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诗的“无邪”性质并不分现代诗和古体诗,顾城就被称为“童话诗人”,兰波的形象也仿佛是现当代诗人的形象代言。现代诗的使命之一,依旧是保留天真、柔弱,以对抗物化、工具化,这也是人永远离不开诗歌的一个原因。当然,汉语的整体语境也不可忽略,经济浪潮和商业文化的冲击对语言的改变和影响也非常大,这时就更需要现代诗人这样的语言祭师,通过诗歌写作保留对汉语的尊重,保持语言经典性的自觉。
杨键:没有经学做底色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
余退:“经者,常道也”,经典之学是人类文明的精粹部分。缺乏经典文化熏陶的人生,“质胜文则野”,不能温润。而缺乏诗意和诗歌的人生,很容易器化,不能体会作为人的富足。
杨键:没有经学做底色的家庭会是什么样的?
余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经学是作为家庭的基础、背景而长期存在。所谓“诗书传家”,典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诗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下,作为生活方式,“晴耕雨读”已不好实现,但是作为安顿的力量,经学一直以来是以后也必将是家的文化内核。很难想象,如果犹太民族缺少《圣经》的护持,还能不能大量现代犹太文化精英的出现。中国也不例外,如果缺少经典护持之力不足,家的成立也必将非常艰难,这个并不分古今。
杨键:没有经学做底色的文学会是什么样的?
余退:中西方文化各互有经典护持,形成所谓“文脉”,目前正处于世界文化会通之际,文学的交融现象也非常显著。文学既是文化本身之一种,离开经典无所谓文学,孔子评价弟子中有“文学”一科,《四书》本身就是非常优美的文学范本。当下,汉语文学的处境和世界上其他语系文学的处境也是有同有异,但总体而言缺乏精神谱系的文学是虚弱的。
杨键:新诗语言的戒定慧,新诗语言的仁义礼智信,如何才能建立?
余退:从“仁”字切入可能容易讨论一些,“仁”涵盖义礼智信戒定慧等诸义。“仁者,人也”,新诗的语言就是人的语言,言为心声,为人性而发声。所有伪善、虚假的声音都不能代表真正的人声。新诗语言秩序建立的背后是对人性的理解尊重发扬,是人格的建立。只要视界范围内的人性尚未被真正阐发、理解、尊重,写作群体成熟的心灵尚未建立,新诗语言的建立就不能够完成。
杨键:与旧诗相比,新诗的道的面容没有出现,自然的面容没有出现,德的面容没有出现,你如何看这些问题?
余退:“神无方而易无体”,道在万物之中,变化多端,新诗的面容肯定有别于旧诗,或许在目前而言尚不够清晰,但不会离道。符合写作之道的诗歌,自然会诞生出相应的道、德的面容,只是与旧诗相比,一则可能尚不成熟,二则面容不同。诗歌只要是真诚之作,不论优劣,都是“道”的表现。
杨键:儒教影响下女性会影响旧诗的发展吗?
余退:儒教影响下女性造就了旧诗的发展。《诗经·关鸠》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句子,很明显首先是出于对美丽女性的爱慕之心。但如果女性仅仅作为诗歌创作的对象和素材,那还只是外因。可能更准确的说法是,古代女诗人造就了旧诗的发展,比如李清照、蔡文姬、谢道韫等,《红楼梦》中大观园对诗一节非常精彩,黛玉、宝钗、探春等的诗歌都非常精彩,各展示了其内心境界,那代表了被雪藏了的无数诗意女性。
杨键:没有儒教影响下的女性会影响新诗的发展吗?
余退:当代女性诗人对新诗发展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近代诗歌史上诞生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艾米莉·狄金森、普拉斯,乃至刚获诺奖的格丽克等众多知名女诗人。目前,国内女诗人比例也非常高,对新诗发展已经也将继续造成深度影响。不管当代女性受儒教程度影响如何,作为在场者,都直接进入了诗歌写作的中心。
杨键:自我不能泯灭,写诗只是一种不易觉察的自恋,你认同吗?
余退:“无我”建立在自我的确认之上,具有超越义。“诗”本身也具有强烈的超越性质,使得很多诗人显得不切实际,诗仙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多少与现世格格不入。自我不可泯灭,诗歌的存在,促使人通过诗歌实现自我审视和自我发现,而逐渐超拔。“恋”字由“亦”“心”组成,视恋人之心亦如己之心,真正的“恋”,推己及人,琴瑟和鸣,肯定是超越“自恋”的。诗人因迷恋世界、人类、未知而显得可爱。
杨键:你现在对“诗言志”这个古老的教义如何看?
余退:“志”者,志向,志趣,志业,具有非常强烈的精神向度。现代人的志趣和志向指向多元,表现的形态就会多样化,但同样需要具有强烈的精神向度,这个或许是现代人所缺乏的。
杨键:新诗里有太多的情绪,大抵还没有上升到智慧的层面,你对此如何看这个问题?
余退:情性、情感、情绪,人是具有感情的生物,情绪的表达是人具有的最基础的机能。儒家讲“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以智慧对待自己的情感、情绪。“诗言情”,人无法尽情表达的喜怒哀乐之情,会借助诗歌来抒发,是自然而言的,也是“止乎礼”的一种表现。陷溺在情绪之中的新诗,不会是非常好的诗歌。
杨键:汉文明意义上的家还在吗?
余退:汉民族的家是泛指家族。近代史上,汉文明意义上的家,遭到了异常严重的破坏,曾经家谱、祠堂都被当作破四旧的顽物铲除,无疑是经过了劫难。家的记忆是人不可替换的宝库,切断记忆,会造成苍白、迷失。我的家乡是一座小海岛,岛民都是福建泉州及温州一带移民而来,岛上少有宗祠。在不久的几年前,我才第一次到瑞安和苍南参加了曹氏宗亲的祭祖仪式,走进了宗祠,很自然涌现了一股难说清楚的感动。
杨键:汉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人还在吗?
余退:我所理解的华夏文明一直就是混血的,我的家乡温州,古时建立东欧国,恐怕就是属于南蛮之地。我讲的方言是闽南话,闽南文化笃信鬼神,多有神秘元素,不能归入正统文明序列,却依旧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近代以“儒释道”为中心的华夏核心文化更是又一次遭遇了劫难,儒生的消亡就是一大表现。不管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是否还在,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处境,需要处理的题材。我在我的诗歌《迷船》里也写了这样的现实境:“这恐怕就是我这位/渔三代的天命:拼接一艘迷船”。
杨键:三字经言“非圣书,摒勿视”,圣贤之言本是汉文明的核心精神,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对此,你如何看?
余退:三字经“非圣书,摒勿视”,是对学童劝学之言,引导其形成分辨力。《中庸》里的学习方法更加中正一些,“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汉文明的核心精神是复合的,有主线,也有辅线。“子不语怪力乱神”,而生养我的闽南文化恰恰充满了怪力乱神。从文化角度上理解,这些“怪力乱神”都深深保留着我们先祖的部分记忆,并且关系到我们的来源。我也逐渐明白了为什么卡尔维诺愿意化很多时间去收集、整理《意大利童话》。
杨键:汉语的声音,说到底,有四个特点,一是求道之声。二是赤子之声。三是自然之声。四是归于自性之声。这四种声音今天都非常微弱了,我们如何才能回归汉声呢?
余退:语言的背后是心灵,随着心灵的成熟和自觉,自内而外,因有感触震颤就会发出属于它自己独特的声音,或为歌,或为诗。看似汉族是华夏多民族里不善歌舞的民族,实则是因为诗词曲赋兼具了吟诵传颂的功能,转为心灵的歌唱。只要有诵读诗经汉赋唐诗宋词之处,求道、赤子、自然、自性之声就依稀若存。“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古体诗的处境也堪忧,也在于现代词人的境界问题。而现代诗因其具有强烈区别于古体诗的特点,其显现的境界全然不同,可能汉声之味尚不足,其背后还是有待具备现代意识的心灵的完善,以至于心性的通达。面对真实,在新旧碰撞、中西会通的背景下,现代诗人心灵之境的锻造,必定会是一个复合、漫长的过程。
杨键:请谈谈诗歌与修行之间的关系。
余退:写诗既修行,依靠语言这一工具,写作者的幸运,就是拥有另外一条通往自己的暗道。和其他修行一样,写诗时需要面对孤独之境,需要“慎独”,要有极度的耐心、克制力。阿多尼斯语“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诗歌写作经常带你走进荒原,你能开垦的工具唯有语言和心灵。近来喜爱徒步,深山环抱中常藏有一座不大的古寺,香火未曾断绝,有一两位出家师在驻守。诗歌写作犹如修庙、守庙。
杨键:立德,立言,立功,你选择哪一样?
余退:对于“德,言,功”而言,个人更看重“立”字。孔夫子三十而立,下学上达,自立,独立,不再退转,谈何容易。马拉美说“世界的目的就是一本书”,对于诗人,多少会有立言的倾向,这里的“立言”和儒者的不一样,但或许终其一生都不会有一句半句诗歌能够留下来。关键还在于心灵的建立。
杨键:文明是舍身饲虎,你认同吗?
余退:我感觉这种说法是一种比喻,说的是推动文明需要勇气、仁爱。“智仁勇”是三达德。写作是需要勇气的,面对真相,面对人性,面对自我,也是培养诗人之爱的途径。
杨键:古典诗歌的背后是君子人格,新诗的背后是什么呢?
余退:新诗的背后依旧是君子人格,不过表现形式不一,人格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展现。新诗人格的内涵有更多未被定义的内容,因为面临的情境不一样。人是始终不能被完全定义的,新诗的存在关联人的存在,很多时候意义是需要自我赋予的。
杨键:就目前而言,新诗的根基还是欲望,仇恨和无明,新诗的清净心远未出现,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余退:“无明”无根,理论上新诗的根基只能建立在自由、独立、自我的发现等当代精神之上。欲望、困顿、仇恨都是表象,背后是现代人类在自我发现的过程中洞察到无数的“空无”而产生了诸如幻灭、虚无等认识。就像理解“垮掉的一代”并不只是简单的“垮掉”一样,中国新诗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仅百年的发展史几经波荡和断裂,新诗真正根基的奠定还需要时间,需要无数新诗人们真诚、勇敢、智性的写作。
杨键:人生短促,很快死亡就会来临,你认为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吗?
余退:文明存在的很大原因就是面临死亡,文学的存世价值也是因为此。正是因为死亡马上要来临,所以人类要迫切地质问。面对更为根本的问题,才会有哲学、文学、生命学等学科的出现。辛波斯卡《写作的喜悦》里写到“写作的喜悦/保存的力量/人类之手的复仇”,文学伴随着死亡而生。比文学更重要的或许是心灵的觉悟,“朝闻道,夕死可矣”肯定是一大超越的境界。
杨键:苏东坡对黄庭坚的评价是:“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这样的超轶绝尘之作新诗至今没有出现,对此,你如何看?
余退:新诗之创成,需要时间与沉淀,新诗也有其独特的性格正在形成。超轶绝尘之作,有赖于唐宋儒道释等主流文化的发达。如若近当代中国思想之建树成型,具有现代意识的独特人格建立完成,相应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都将诞生,包括诗歌,但其表现形式可能有异于“超轶绝尘”,带有一些未知的成分。钱钟书批评“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而留给新诗的空间即是变化。
杨键:汉语诗歌同英语诗歌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余退:中西世界差异是个大命题,汉语诗歌同英语诗歌的差异很多,语言特点、题材内容、思维逻辑、精神谱系都不一样,可能最大的差异还是在于文化的来源,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尤以儒家为代表,而西方文化的来源在古希腊,和基督教的精神密不可分。但从更大的视角来讲,诗歌发乎本真,阐发人性之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人”所写下的诗。
杨键:欢乐是肉体带来的吗?
余退:肉体之乐非恒常之乐,其背后是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灵肉是二又是一,肉体和精神高度关联。文化的高贵,在于处处受限的肉身发掘出精神的无限空间和维度。很多微妙的情境并不在肉身世界中存在,比如你难以用冰冷的仪器去测量仁和爱,但是却很容易被有情之人一眼洞穿。写作有写作的独特乐趣,沉浸在写作之中,有时会出现“心流”现象,时间消失,物我两忘,乐以忘忧,不知身在何处。当然“心流”消失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杨键:汉语的欢喜心如何获得?
余退:语言犹如舟楫,想获得划桨荡漾之乐,先要试着划桨,这时会发现欢喜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熟练地把握木浆,感受水流,读懂航海图,掌握节奏都是一名桨手的基本功。处理汉语时亦然,理解当代汉语的复合属性,锻炼心灵,保持敏感,都是获得欢喜心的前提条件。这也是个人不再迷信写作依赖天赋的原因。
杨键:你如何看待“恕”字?
余退:“恕”字拆解开是“如”“心”,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个人对待外境现前的一大素养。
杨键:你相信因果吗?
余退:因果是世界的客观规律存在之一。有因有果,连绵不绝。
杨键:人死如灯灭吗?
余退:生死依旧成迷。“不知生,焉知死”,对于死亡及一些神秘领域,儒家存而不论,但又极端重视葬礼、祭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一种高度的智慧表现。生死学也是目前的一门前沿学科,里面包藏了太多含糊和未知的地带。人死是否如灯灭,是未知的。

杨键简介
1967生于安徽马鞍山。诗人,艺术家。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曾出版诗集《暮晚》《古桥头》《惭愧》《哭庙》《杨键诗选》。先后获得首届刘丽安诗歌奖、柔刚诗歌奖、宇龙诗歌奖、全国十大新锐诗人奖、第六届华语传媒诗人奖、骆一禾诗歌奖、袁可嘉诗歌奖,小众诗歌奖。多次举办过水墨个展及各类群展。
杨键个人画展:2011年 《杨键的水墨》 (南京艺事后素美术馆),2013年 《道之容颜》(北京今日美术馆),2014年《冷山水》(深圳关山月美术馆),2015年《寒山》(常熟虞山当代美术馆)。近年来杨键参与的重要画展: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虚薄之境——对画:山水与风景、峨眉当代艺术论坛“黑白进化论”展、第二届南京国际美展水墨主题展、大运河国际诗歌节暨当代诗人书画展、蔑视与叹息、新人文画五人展、仰而思之——岛子申伟光杨键三人展、灵性的回归——中国当代诗人绘画巡回展、自由的尺度——中国当代水墨走向欧洲、深圳 、尘尽光生、生生——洪凌杨键艺术联展等。
生生对话专辑●●
……

生生之境公众号
微信号 :the_state_of_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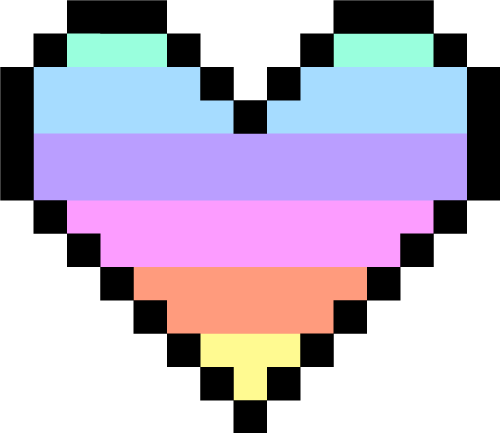
点“在看”给我一个小心心







